 《风景》系列之三
《风景》系列之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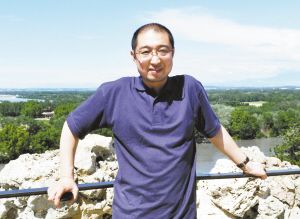
商报:相比以往的《风景》系列作品以点、线为主要架构,色彩运用方面选择了单一的灰黑调子。近期的新作品系列《消逝的风景》,无论用色还是绘画对象的具体阐释,都要更加丰富并具有层次感。
饶松青:这是两种反差极大的绘画语言形式,但却完整地描述着我艺术生活的两个方向。我始终在坚持“双线并行”的艺术创作思想,这两种风格在视觉上的冲突很大,但却拥有统一的脉络,两条线索形成各自的语言方式,最终表达的是共同的主题。早期的作品基调晦暗,作品中流露出苦闷、焦虑、孤独的生命形态,它呈现了个体生命在一个价值多变、命途多舛的时代,内心的惶恐与不适。作品中的孤独感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孤独,还有对未知的好奇与无助,对命运无可把握的茫然无措,这是一种体验“存在”本质的“孤独”。
近期的《消逝的风景》系列作品亮丽淡雅。时而灿烂,时而凄冷,同时兼备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点彩。作品强烈呈现出属于东方艺术家的美学根源与向往,这是陶渊明式的东方文人情结,也是一种在矛盾中求证自我内心和谐的生命诉求。
商报:从绘画语言的表达形式上,您如何看待这两条创作线索?
饶松青:在艺术形式上,这两种看似反差很大的作品实质互相矛盾、互相补充。它同时展现了我内心的现实与梦想,可以看成是一件完整的观念作品。“艺术是生活的味精,多了矫情,少了寡淡无味。”
商报:早期作品里对点与线的着重强调是一种形式上的刻意抽离吗?
饶松青:这与我当年在圆明园时期的生活感受相关,北京的冬天干燥而冷清,树木的枝枝杈杈使得整个氛围显得分外萧瑟,会让人产生无论在哪个角度看都会无限延伸的疏离感,如同你看远处会有一个终点,但越往前行,终点便越前行不止,永远无法靠近,我只不过是用绘画中的点线方式将这种概念提纯出来。
商报:您的油画作品里渗透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文人情怀。
饶松青:我始终坚持在东方的文化气质里面寻找某种可以延伸的情感表达,也在考虑东方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到底有多大的可塑性与可能性,东西方绘画在艺术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性,东方绘画强调情怀的转述,借物咏怀、寓情于景等手法皆是艺术家在传达自身的一种生存感受与内在人格,与西方那种客观对照物象的方式具有很大区别,这跟东方人骨子里的主观感性因素是分不开的。
商报:您怎样理解包括架上绘画在内的艺术的功能性?
饶松青:艺术不仅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,还应具有对视觉经验的探索、传播媒介的延伸与拓展,对人生存体验的深度挖掘等多重功能。
商报:据了解,您爱好收藏石刻,您绘画中的灰黯色调与古朴而厚重的实质相得益彰,这其中是否有着微妙的联系?
饶松青:两者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存在,其中必然有相近的本质存在。
商报:您的绘画作品中渗透着强烈的观念性,您怎样看它与绘画性之间的关系?
饶松青:优秀的艺术家会找到合适的艺术语言方式进行表达,这涉及到语言技巧,我们在创作中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恰恰是如何准确而有魅力地表达,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已积累并且形成,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表达。但当代艺术对技术层面的变革过于依赖,这是科学精神对艺术指导的延续。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当代艺术对传播媒介的延伸与拓展过度关注,同时对精神层面的深度挖掘却日趋匮乏。因此我们还面临一个课题,那就是如何确认并建立与当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。
商报:面对近几年来艺术市场对艺术符号性的注重,您如何看这种现象?
饶松青:艺术家不应只拥有某个单一的创作体系,尽管当今主流似乎认为成熟艺术家要形成一套固定的艺术模式,实际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,可能会有几条并行的艺术轨道。同时我个人认为在艺术上不应有过多个人英雄主义情结,因为它所具有的排他性会成为我们对民主文化诉求中的障碍。艺术应该是多元化、百花齐放的,多种声音才能构成健全的艺术生态体系。
绘画是一种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,有漫长的发展史,它在语言本体拓展所提供的空间有限,只能更多地从生存体验的深度挖掘对当下社会情境的呈现,去体现她在当下的意义。商报记者 丛晓燕